Study on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Dongting Lake Area
-
摘要: 洞庭湖在晚冰期以来经历了多次变化过程.晚更新世末至早全新世呈现深切河谷与零星洼地湖泊共存的河湖切割平原景观. 进入全新世暖期, 人类活动开始在洞庭湖平原地区频繁出现, 新石器时代皂市文化分布表明人类活动主要在洞庭湖周边地区; 大溪文化时期人类已在平原湖区中部开始渔猎活动; 屈家岭文化时期气候转暖, 洪水开始泛滥, 人类活动从洞庭湖平原中部退出; 至龙山文化时期, 气候干燥偏凉, 降水减少, 人类文化活动遗址向湖中推进, 湖泊三角洲有所发展, 湖面缩小.在以后的几千年里, 洞庭湖也同样经历了扩张与萎缩的变化.Abstract: The Dongting Lake has experienced several change processes since last glaciation. From later Pleistocene to early Holocene, the Dongting Lake area was a plain cutting by deep channel. Then the anthropologic has been to the Dongting Lake area frequently since the globe change warmer in Neolithic time. The Zaoshi civilization shows the human activity almost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Dongting Lake area and the Daxi civilization indicated the advance to the center of the lake area for fishing and hunting. It was warm and flooding in the Qujialing civilization time, and human being retreat from the lake area. Since the Longshan civilization time, it was cool and precipitation reduced, and human activity moved to the center of the lake area. The lake's delta developed and lake surface decreased. Since the last thousands years, the Dongting Lake experiences the expand and shrink periods several times.
-
Key words:
- Dongting Lake /
- historical period /
- civilization sites /
- environment
-
环境的变化往往制约着人类的生存发展.尤其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数千年前,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 活动空间受环境变化的控制, 因而人类活动的文化遗迹更具有反映当时自然环境面貌的特点, 这也是考古学和历史学能作为研究环境变迁重要手段的依据.长江中游平原湖区是我国古文化遗址丰富的地区, 考古资料极为丰富.
1. 古环境特征
受区域环境变化制约, 洞庭湖在晚冰期以来经历了几次较大兴衰变化过程.晚更新世末至早全新世, 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河流下切侵蚀, 形成深切河谷与零星洼地湖泊共存的河湖切割平原景观[1].
洞庭湖区的大量钻孔资料表明, 晚更新世末到全新世初期湖区广泛发育砂砾石层, 黄褐色、灰黄色粘土质粉砂层以及含铁锰结核、呈黄色与灰白色的粘土、粉砂质粘土层.孢粉分析为干寒气候环境下的沉积物[2, 3].此层在洞庭湖区可作为全新统底界的标志层, 在此层之上堆积全新世的河湖相沉积.
全新世中期自今沅江河口至东洞庭湖有一个近北东向, 宽为17~33 km的长条状蓝绿色粘土带, 多含数量不等的贝壳, 在安乡北部与今漉湖以南亦有较小的分布区, 说明洞庭湖在全新世中期湖沼相堆积同样广泛分布, 也可能存在一个中心地带位于沅江河口至今东洞庭湖的北东向长条状的湖面.而粘土带周围分布粉砂质粘土、粉细砂质粘土及粘土质粉砂类沉积, 表明为洪泛相或滨湖相的沉积[4].
2. 新石器文化遗址分布
洞庭湖区由于气候温和, 降雨充沛,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 远古的人类祖先就在这里生存栖息, 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存.根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最近完成的湖南省文物普查资料和文物普查图集[5], 收集了与洞庭湖相关的13个县市的1 722个文化遗址资料, 其中在湘、资、沅、澧四水下游和洞庭湖区已发现新石器遗址423处, 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体上包括以下4个阶段.
2.1 皂市下层文化时期
第1阶段为皂市下层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澧水中下游沿河丘陵阶地上, 年代范围为7 200~7 900 a, 出土制作简单、粗放的红陶器, 生产工具为采用砾石加工而成的磨制石器, 表明当时的先民利用这里丰富的天然生物资源, 主要依靠渔猎来维持生存.此时为全新世高温期, 降水丰富, 洞庭湖水面扩展, 洪水泛滥, 湖区不适合人类生存.
湖区平原中部亦有个别遗址被发现, 如南县涂家台遗址位于南县九都山乡大郎城村, 文化层自上而下可分为9层, 最底层距地表150~155 cm.据益阳地区博物馆试掘, 遗物主要为陶器, 属于早于大溪文化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根据湖南考古界近期对涂家台遗址150 m2内16座墓葬的发掘, 发现了大量陶器、石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现了长3.2 m, 宽0.6 m的形似独木舟的器物, 说明7 000 a前该遗址在洪水期已为洞庭湖水面扩展所封锁, 独木舟是古人和外界联系的主要工具[6].
如前所述, 从洞庭湖区14C测年为7 000 a左右的沉积物分布来看, 自今沅江河口至东洞庭湖有一个近北东向的长条状蓝绿色粘土带, 多含数量不等的贝壳, 厚度1~3 m.粘土周围沉积则为灰绿或灰褐色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 其沉积特征与现在洞庭湖的湖滨沉积基本一致[4].孢粉分析表明此时的木本花粉占总孢粉量的80%, 其中喜热枫香属占木本花粉的48%, 表明为温暖湿润气候, 相当于大西洋期气候.此时处于全球气候最宜期, 降水丰富, 海平面上升, 长江水位由于河床及自然堤溯源加积而上涨[7], 影响湘、资、沅、澧四水的排泄, 则有可能在原来的河网切割平原上涌水成湖.虽然此时水面扩张, 但由于气候温暖, 环境变化缓慢, 恶劣气候很少出现, 适宜于人类活动的发展, 因而在洞庭湖周围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化遗迹.而大部分文化遗址分布于岗丘区, 说明湖区不便于居住, 分布于湖区中部的少数文化遗址, 如南县涂家台遗址, 位于粉砂质粘土、粘土质粉砂区, 是湖滨岸滩地带或是湖泊三角洲发育后所形成的地势较高部位, 则有可能是少数以渔猎为生的人在湖滨的定居处.此时洞庭湖并不是很大, 基本上位于现在洞庭湖的范围内, 呈现大水时湖面扩展, 水退时河湖交错的自然景观.
2.2 大溪文化时期
第2阶段属于大溪文化, 距今6 000 a左右.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遗址分布广泛, 经初步统计在洞庭湖区13个县市中分布着45处文化遗址, 主要位于洞庭湖周缘及丘陵地区[5], 如湖区西部的澧县彭头山遗址、李家岗遗址、三元宫遗址等; 北部丘陵区的刘卜台遗址、轱山遗址等; 南部丘陵区的蔡家园遗址、河坪遗址等.随着考古界的不断发现, 湖区中部平原区也有多处遗址逐渐被揭示出来(图 1), 如华容县坟山堡遗址、踏地坪遗址、方台湖遗址, 南县涂家台遗址、新湖鱼场遗址、东线遗址, 益阳市石咀头遗址, 益阳县丝茅岭遗址, 汉寿县百禄桥遗址, 湘阴县飘嘴遗址等.
大溪文化内涵与湖北宜都红花套、松滋桂花树、江陵毛家山等遗址的大溪层文化内涵基本一致, 以泥质红陶为主, 用于纺线的陶纺轮这时已经出现.与此时代相当的华容县车轱山早期遗存灰坑中发现成片的炭化大米.这表明进入湖南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 最先定居在洞庭湖北岸, 利用这一带河湖密布、土壤疏松肥沃、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天然条件, 在捕鱼、狩猎的同时, 开始广泛种植水稻, 饲养家畜.并因御寒或捕鱼的需要, 开始纺线结网等原始的纺织劳动.如前所述, 6 000 a为全新世高温期中的降温阶段, 此时气候变冷, 降水减少, 洞庭湖水面收缩, 人类活动开始向平原中心发展.大量大溪文化的遗址在湖区发现, 说明人类活动已经深入到洞庭湖平原区的中心地带.
2.3 屈家岭文化时期
第3阶段与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一致, 距今4 500~5 300 a.洞庭湖区屈家岭文化遗址与大溪文化遗址的分布有着显著区别.湖区13个县市中共发现有60处屈家岭文化遗址, 绝大多数遗址分布在湖区西北部及西部5县市[5], 湖区东部及南部的益阳市、益阳县、南县、沅江市、湘阴、汨罗、岳阳县等7个县市尚未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址(图 1), 岳阳市仅在北部丘陵区发现一处龟形山遗址.说明在距今5 000 a左右, 洞庭湖西部地区的人类活动远较东部强烈, 而在洞庭湖的南部和东部出现了文化间断.据杨怀仁[8]研究, 距今5 000 a左右, 我国属高温多雨时代, 同时也是洪水泛滥的时代, 此时的洞庭湖西部和北部没有太大变化, 东部、南部及中部的范围则由于湘江和资水的泛滥而有了较大扩展, 洪涝灾害频发的环境不利于人类活动的发展.
洞庭湖区的屈家岭文化以泥质黑陶和灰陶为主.华容县长岗庙遗址中除发现了磨制精细的长方形辉绿岩石斧、长条形煌斑岩石钻等生产工具外, 还发现有红陶纺轮.安乡庹家岗下层以黑陶为主, 出土的工具也有磨制较精的穿孔石铲、小石锛及红陶纺轮.这时母系氏族公社正逐步向着父系社会过渡.男劳力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成为主要的生产者, 氏族内部可能已出现了男耕女织的分工.从各遗址出土的工具看, 他们在洞庭湖沿岸及四水流域的丘陵岗地上从事砍伐山林、挖土耕作的劳动.较前一阶段, 此时气候回暖, 降水增加, 洞庭湖水面又一次扩张, 人类退出湖区, 主要集中在湖区西部的丘陵和高台地上活动.
2.4 龙山文化时期
龙山文化在湖区四周及中心部位均较繁荣, 在湖区423处新石器遗址中, 共发现有300处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古遗址[5].如华容北部丘陵区的车轱山遗址、螯山坡遗址、天命咀遗址等28处; 洞庭湖西部澧县有胡家屋场遗址、周家庙遗址等150处; 安乡有横岭岗遗址、划城岗遗址等9处; 津市有青龙嘴遗址、打鼓台遗址等5处; 南部平原及丘陵区, 汉寿有护国障遗址、牛角渡遗址等18处; 益阳有株树潭遗址、塘坡里遗址、大咀坝遗址等44处.洞庭湖中心地带遗址(图 1), 南县附近有新档湖遗址、陈家台遗址等18处; 沅江一带有吼龙港遗址、胜利渠遗址等11处; 洞庭湖东部岳阳、汨罗、湘阴有金星遗址、附山园遗址、北石井遗址等18处.可见龙山文化已由丘陵区大规模向平原湖区推进, 人类活动遍布洞庭湖的大部分地区, 此时的洞庭湖已迅速萎缩, 三角洲迅速发展, 分流间洼地广布, 河湖交错平原成为其时主要景观.
此时洞庭湖区的沉积物主要为分流河道所沉积的灰色、青灰色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细砂, 含腐殖质, 分流间洼地沼泽沉积分布亦很广.根据14C测年约为(3 950±120) a的沉积物钻孔的孢粉分析, 此时孢粉组合为木本占30%, 草本占20%, 孢子占50%.木本以软木松为主, 有较多的栎, 少量青冈、桦、亚热带阔叶树种和零星云杉; 草本以蒿和其他水生植物为主, 孢子以水龙骨为主, 木本植物所占比重明显小于前期, 表明气候转向温凉, 相当于亚北方期[3].此时降水减少, 流水作用减弱, 长江水位下降, 河道比降加大, 洞庭湖区四水易于渲泄, 广阔的水面被分割成三、四个较小水面, 分流间洼地沼泽分布较广, 呈现河湖切割平原景观.
2.5 华容车轱山遗址
华容车轱山遗址连续经历了上述3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是一处文化堆积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的遗址.车轱山遗址在华容县城以东15 km三封乡毛家村, 遗址四周原是浅湖平原, 现均辟为农田.遗址呈不规则多边形, 面积约1.0×104 m2, 发现有房屋建筑基址及储存大米的窖穴.最具规模的是氏族公共墓地, 在已试掘的不到300 m2的范围内, 清理墓葬竟达三、四百座之多.遗址有6个自然地层, 文化层厚2~3 m, 说明这里曾为一长期而稳定的居住生活区.早期遗存以泥质红陶为主, 次为夹砂红陶, 全为手制, 陶片中有时可见烧成黑炭的谷壳; 中期遗存以泥质黑陶、灰陶为主; 晚期以夹砂红陶为主, 泥质灰、黑陶次之, 仍以手制为主, 但出现了快轮技术.房屋基址以烧红土为墙壁和居住面, 烧红土中发现掺有稻谷和稻草.早期遗存的窑穴中, 发现有成堆已炭化的大米, 其颗粒形状仍可辨认.这些大米, 应是当时贮存于窑穴里备用的粮食.公共墓地的墓葬排列密集, 上下叠压, 全为一次性单人葬.随葬器物中, 石制生产工具有斧、锛、铲等, 其中石斧在早、中、晚期遗存中均可见到, 不少有安装木柄使用的砍痕及磨损痕迹; 石铲的数量最多, 见于早、中期遗存中, 除少量有琢钻单孔外, 多数为管钻法两面对钻的单孔或双孔, 时代越晚, 钻孔越规范.此外, 还出土有陶制纺轮及石制的渔猎工具等.随葬的石斧、石铲及其他石制工具, 绝不与纺轮共存.保存完整的骨架中, 凡有纺轮随葬的, 女性特征明显; 凡有石制工具随葬的, 男性特征明显, 表明当时已有男耕女织的明确分工.
车轱山遗址中由古代先民所创造的这些文化, 说明新石器时期人们已在洞庭湖滨湖地区过着定居生活, 他们从事原始的农业劳动, 从事稻谷栽培, 并利用谷壳、稻草和泥建筑房屋, 以谷壳为掺和料烧制陶器, 此外辅以渔猎、畜牧业作为生活来源的补充.
车轱山遗址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3个阶段的文化遗存, 通过墓葬挖掘发现, 龙山文化覆盖在屈家岭文化之上, 屈家岭文化早、中、晚3期序列清楚, 其间没有明显的缺环; 大溪文化墓葬直接叠压在屈家岭文化早期墓葬之下, 2种文化有直接的承袭关系.车轱山遗址稳定连续的存在, 说明从全新世高温期到龙山文化时期, 洞庭湖湖面从没有超出过华容现在县城以东的范围, 更不可能存在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
许多研究者[2, 3, 9]都曾利用洞庭湖区的新石器遗址探讨过洞庭湖的演变问题, 受当时考古资料不够完整的限制, 只是笼统地把洞庭湖区的古文化遗址称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没能对新石器遗址几个阶段做进一步的划分, 从遍布全区的新石器遗址分布得出从全新世初至公元三世纪为河网切割平原景观.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石器时期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等各个阶段的古文化遗址的数量不同, 分布范围和区域也存在明显差异, 表明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随着湖泊环境的变化有过多次进退, 正说明了湖泊环境演变的复杂性.洞庭湖区的环境在这几千年中也并非一直都是河网切割平原景观, 而是经历了湖泊扩展与河湖切割平原的多次变更.
3. 全新世环境演变
经过盛冰期后短暂的晚冰期和全新世早期的波动式温度回升, 长江中游地区的气候迅速进入全新世气候最宜期.在约7 500~6 000 a, 气温较现在高出2 ℃左右, 雨量充沛, 海面上升至现在高度或略高于现在高度[10]; 以后温度又几经冷暖高低变化, 但再也没有出现过冰期和间冰期般的剧烈起伏.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洞庭湖区随着各入湖河流来水量的变化和地面继续沉降, 湖泊水面有过多次扩展与收缩, 在晚冰期至全新世早期形成的粗颗粒碎屑充填物之上, 平原洼地区广泛沉积细颗粒物质, 表现为湖沼相粘土淤泥沉积和洪泛相及漫滩相的粉细砂堆积.另外, 全新世中晚期以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人类在平原湖区的活动逐渐增加, 人类在受制于自然的同时也努力改造着生存环境, 使洞庭湖区的全新世中晚期环境演化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 这也为研究全新世环境演化提供了途径.
东部海面上升引起长江河床与自然堤的溯源加积, 导致长江两岸形成壅塞湖, 此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成湖期, 如武昌东湖的形成是由于长江自然堤对早期支流谷地的堵塞[11].江汉平原亦出现全新世以来的第1次成湖期, 出现星罗棋布的河间洼地湖和壅塞湖[12].全新世高温期, 洞庭湖在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形成的河谷深切平原基础上, 普遍出现了河湖充填地貌景观.洞庭湖区由于长江水位的上升及长江河床的抬升, 阻塞了洞庭湖水系的排泄, 湘、资、沅、澧四水汇注洞庭盆地, 壅塞形成开阔水面.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高温多雨的时期, 水面扩展, 人类活动向湖周丘陵和高岗地发展; 在低温少雨时期, 湖泊水面退缩, 人类活动由山地和丘岗区向湖区中心推进.杨怀仁[10]曾论述了全球气候变冷与海面下降、海岸淤长以及区域湖泊低水位之间的同步关系.全新世中期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和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的分布都说明了洞庭湖演变的反复性.水面扩张时期洞庭湖水面的中心地带为沅江河口至今东洞庭湖, 呈北东向长条状分布, 与古沅江深切河谷位置基本一致.汛期水面连成一体, 四水带来大量泥沙, 在河口地区沉积开始发育三角洲; 枯水期长江水位下降, 湖面相应收缩, 大面积滨湖滩地裸露.
中全新世晚期, 随着三角洲的发育及湖水退缩, 广阔的滨湖滩地裸露, 平原湖区以分流间洼地沼泽并存为特点, 其沉积主要为分流河道所沉积的灰色粉砂质粘土及细砂, 分流间洼地沼泽沉积的粉砂质淤泥与淤泥质粉砂, 龙山文化在湖区繁荣.在这之后进入有史料记载的历史时期, 洞庭湖亦多次发生变化.
-
[1] 杨达源. 晚更新世冰期最盛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环境[J]. 地理学报, 1986, 41 (4): 302-31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LXB198604001.htmYANG D Y. Paleoenvironment of the mid-lower reg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full-glacial period of Late Pleistocen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86, 41 (4): 302-310.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DLXB198604001.htm [2] 周国琪, 成铁生, 赵守勤. 洞庭湖盆的由来和演变[J]. 湖南地质, 1984, 3 (1): 54-6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NDZ198401006.htmZHOU G Q, CHENG T S, ZHAO S Q.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Dongting basin[J]. Hunan Geology, 1984, 3 (1): 54-6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NDZ198401006.htm [3] 闾国年. 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M]. 北京: 测绘出版社, 1991.LΓˊ G N. Lake basin deltas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geomorphology re-exposition and simulation in th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M]. Beijing: China Survey Press, 1991. [4] 张晓阳, 蔡述明, 孙顺才. 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J]. 湖泊科学, 1994, 6 (1): 13-2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LKX199401002.htmZHANG X Y, CAI S M, SUN S C. Evolution of the Dongting Lake since Holocene[J]. Journal of Lake Sciences, 1994, 6 (1): 13-2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LKX199401002.htm [5] 湖南考古研究所.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M]. 长沙: 湖南地图出版社, 1997.Institute of Hunan Archaeology. China cultural relic atlas—Hunan branch[M]. Changsha: Hunan Atlas Press, 1997. [6] 张翼飞. 考古发现江南最早墓葬群[N]. 长江日报, 1999-4-18 (3).ZHANG Y F. Archeology found the earliest tomb in the south part of the Yangtze River[N]. Changjiang Daily, 1999-4-18 (3). [7] 方金琪. 晚冰期海面上升对长江中下游影响的探讨[J]. 地理学报, 1991, 46 (4): 427-434.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BXK199008012.htmFANG J Q. A pilot study on the impact of postglacial sea level rise o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J]. Acta Geographical Sinica, 1991, 46 (4): 427-435.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JBXK199008012.htm [8] 杨怀仁. 末次冰期以来的长江[A]. 见: 杨怀仁. 环境变迁研究[C]. 南京: 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6.328-334.YANG H R. Changes of the Yangtze River since the last glaciation[A]. In: YANG H R, ed. Study of environment changes[C]. Nanjing: Hehai University Press, 1996.328-334. [9] 卞鸿翔, 王万川, 龚循礼. 洞庭湖的变迁[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43.BIAN H X, WANG W C, GONG X L. Evolution of the Dongting Lake[M].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1993.43. [10] 杨怀仁. 中国东部近20000年来的气候波动与海面升降运动[J]. 海洋与湖沼, 1984, 15 (1): 1-1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YFZ198401000.htmYANG H R. Climate changes and sea level movements in East China since last 20000 years[J]. Oceanologla et Limnologia Sinica, 1984, 15 (1): 1-13.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YFZ198401000.htm [11] 蔡述明, 官子和, 孔昭晨, 等. 从岩相特征和孢粉组合探讨洞庭盆地第四纪自然环境的变迁[J]. 海洋与湖沼, 1984, 15 (4): 527-53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YFZ198406003.htmCAI S M, GUAN Z H, KONG Z C, et al. Natural environment as reflected in sedimentary facies and sporo-pollen assemblages in the Quaternary Dongting basin[J]. Oceanologla et Limnologia Sinica, 1984, 15 (4): 527-538.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YFZ198406003.htm [12] 蔡述明, 官子和. 跨江南北的古云梦泽说是不能成立的——古云梦泽问题讨论之二[J]. 海洋与湖沼, 1982, 13 (2): 129-14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YFZ198202003.htmCAI S M, GUAN Z H.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ancient Yunmena swamp across the Yangtze River—discussion of the ancient Yunmena swamp (2)[J]. Oceanologia et Limnologia Sinica, 1982, 13 (2): 129-141. https://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YFZ198202003.htm -











 下载:
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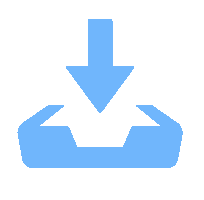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